2016年12月15日晚,导演赵青带着《我只认识你》登上了广州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金红棉奖的领奖台。典礼上她一袭朴素白衣,却收获了三项大奖的空前荣誉:“年度最佳纪录片”、“最佳纪录长片”及“最佳国际传播中国纪录片”。
对于导演赵青、制片人冯都来说,这的确是一份惊喜。《我只认识你》讲述的是她们的亲人——叔公叔婆的爱情故事:这对相识于五十年代,在时代的浪潮中经历悲欢离合的老人,却在迈入古稀之年的时候遭遇了“空巢”与“阿尔兹海默症”的双重困境。
如何在衰老、病痛、孤独的情况下守住爱与尊严?影片给出的答案是最日常不过的细节:患病的叔婆味芳忘记了一切,却唯独记得爱,时时刻刻寻找自己的丈夫;记得爱美,喜欢梳头、别发卡、带手帕;记得阳光,反复晒衣物。而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树锋,在帮妻子准备衣服的时候,还自言自语地说“绿的配绿的”。

树锋在帮味芳穿衣
关注老人的影像作品有很多,但这部片子有一点特别。与沉重的心酸不同,《我只认识你》带给观众的,是一种温暖而克制的感受。但赵青和冯都认为,这种温情并不是自己有意为之的选择,而是老人的生活自然呈现出的动人细节。与此同时,拍摄亲人也给赵青带来巨大的挑战。对于标榜“真实”“客观”的纪录片而言,这样的题材往往被视作一种冒险。
但《我只认识你》不仅仅关于爱情。在影片之外,赵青所在的大家族,自二十世纪初便定居上海。树锋、味芳这代知识分子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历经文革、下放的动荡遭际却依然保持着为人的尊严。在赵青看来,叔公是真正的“仁爱”之人,这样的人,才能够这样去爱。
更多精彩:

年轻的树锋与味芳
与此同时,影片还关注阿尔兹海默症、空巢老人的社会议题。赵青和冯都在两年间已经与多家机构合作,组织了百场公益放映。观众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家属、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医院的医生和药厂的科学家。每次放映会,两人之一都会亲自到场。对于这对年龄相差九岁,但殊途同归的表姐妹而言,拍纪录片都不只是一个项目,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过这种生活,意味着“你要不断进入到别人的世界中,从一个人身上看到更多人的影子,体会他们的价值观和内心的力量。”如果你问,理解他人,这重要吗?冯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非常非常重要。”
《我只认识你》既是赵青和冯都人生轨迹的奇妙汇合,也是中国纪录片代际传承发展的一个例子。谷雨对她们进行了一次访谈,了解这对姐妹的拍摄心得和影片之外的影人故事。
没有绝对的客观和真实,关键是要把握一个“度”
谷雨:最初是因为什么机缘,姐妹俩想合作拍摄一部纪录片?
赵青:我不做纪录片也有很多年了,但纪录片一直是内心无法割舍的一个情结。2012年刚好通过冯都参加了CNEX和圣丹斯合办的纪录片工作坊,受到了很大触动。
冯都: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要拍什么。因为是姐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身边的事情,想到我们冯家大家族。大家原来都住在安顺里的一个弄堂里,当时正好面临拆迁。就很顺理成章的沿着这个线索挖下去。
谷雨: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要拍的主题是叔公叔婆的“爱情”故事?
赵青:最初我们真的没有想太多。叔公是我们家族中最年长的长辈,原来是想从他身上引出更多的人物和故事来。刚开始拍摄,叔公叔婆的状态不是特别好,我就让他坐下来讲两个叔婆前后的故事,包括家族的一些故事。从听故事开始,我慢慢和他们接触多了,越来越能感受到两位老人之间的情感:叔婆患病很多年了,叔公对她就像平常人一样。非常耐心,风趣幽默,又有爱意。渐渐的这些情感侵入到我的内心,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讲述的东西。

树锋照料味芳的生活起居
谷雨:决定拍摄的时候,叔公一开始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抗拒?
赵青:当拍摄触及到日常生活,尤其是叔婆比较病态的状况之后,叔公还是有点紧张。因为像叔公这样老派的知识分子会觉得这是一种家事、是隐私,不应该完全呈现在外人面前。我的一些提议,比如在他们家里住,或者只放一台摄像机在家里,他都拒绝了。但是因为叔公身边没有子女,没有小辈,我拍的久了之后,他反而觉得“你来拍拍我们好像也挺有乐趣”;另外他们那段时间遇到很多困难,觉得可以跟我商量,在这之后就顺利起来。
谷雨:他真正完全理解和接受你们是什么时候?
赵青:是在CCDF拿了最佳提案奖之后。我第一时间去告诉他:他们两人之间的爱、对生活的态度感动了很多人。叔公是一个很明理的人,理解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意义之后,就接纳了下来。
谷雨:有人说老人题材的影片经常让观众感到很难过,很心酸,你们的这个角度传递更多的是温情。
赵青:许多温情的细节都是源于他们的真实生活。比如说叔婆虽然失去记忆,不认识所有人,但就认识我叔公;叔婆生活不能自理,但是还是爱梳妆、别发卡,发卡丢了就很着急;比如爱用手帕,随手就会掏出来;比如她对阳光的热爱,会把已经晒干的衣服再拿出去晒一下……这些细节都是在剪辑的时候发现的,是自然流露的。

爱美的味芳在寻找发卡
冯都:很多人说拍纪录片要找好的角度,但其实角度不是用脑子想出来的,而是深入下去之后,拍摄对象自然传递给你的东西。这些细节在你没有任何杂念的情况下打动了你。如果能够打动到你,那也应该能打动观众。
谷雨:赵导曾经提过,拍这部片子最难的就是你作为导演、又作为小辈,如何和他们相处?具体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赵青:对。叔公有一次生病,叔婆在医院闹,他就打电话想让我去帮忙。但我的第一反应是拿起摄像机,赶去医院。把叔婆带回家之后,我第一次看到没有叔公陪伴的叔婆,那一段就拍摄而言是非常棒的,但是事后我冷静下来,就会质疑自己:“怎么第一反应是拿起摄像机而不是帮助他们处理问题?”还有一次,是陪他们去一家养老院试住,没想到叔婆状况那么糟糕,不停叨叨。叔公一开始还反复解释,最后就沉默地坐在那里。我看到他神情的时候,实在是无法再拍下去,就躲到卫生间去哭。那是我第一次失控。叔公三天之后说“我要回去”,我二话不说就告诉他:“你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做。”我觉得那才是最真实的。
冯都:我觉得“收敛”这个词很重要,这一点上我姐把持的特别好。可以看到导演对两位老人的态度是非常尊重的,正是这种收敛才能产生一种很大的力量,会令人敬畏。
谷雨:对于拍摄亲人,一直存在很多争议。有人认为一开始就应该多拍身边人,也有人认为这样很难拍好,你们怎么看?
赵青:不管是拍身边人还是外人,都要去掌握这个度。不能因为是身边人就情感泛滥,要秉持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
冯都:在国外念纪录片,老师会说:“拍自己家里的故事是大忌,很多时候是失败的。”倒不是因为拍不好,而是大家往往觉得自己的东西才是最有意思的,忘记了和观众的连接性。但叔公叔婆的故事不同,它承载了社会责任的问题、养老的问题、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而不只是关于两位老人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社会价值,叔公最后才会接受我们的拍摄,否则他会觉得自己个人的生活很日常,没什么好拍的。

树锋、味芳参加2015年的上海点映
谷雨:那么如何理解纪录片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赵青:从导演的角度来说,没有绝对的客观和真实,无非是你在情感和客观之间去把握好一个度。如果你跟拍摄对象没有情感的交织点,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动你,你也不可能去拍摄它,意义不存在。关键是导演不要让你的选择和想法介入太多。虽然作为小辈,我很多时候无法冷静面对他们碰到的事情,但还是一切尊重叔公的决定,我跟叔公说:你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冯都:“真实”之于纪录片是指:我不造假,我不会让他们这样走路、这样吃饭。但纪录片是个故事,既然是故事就一定会有导演的观点,所以不可能是纯客观的,一定是主观的。所谓的“客观”是说拍摄对象不是刻意捏造出来的,那样的片子也完全没有力量。但是导演的观点和片子的故事要相吻合。一个常见的反例是纪录片的配乐:情绪还没有到那里,音乐就哗哗加上去。这就是表达的情绪超过了故事本身,那就是过了。
像一个石子,在不同的层面激起对话
谷雨:听说你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可以具体谈一谈吗?
赵青:杨紫烨老师是我们的监制,钱孝贞老师是我们的剪辑,帮助都很大。杨紫烨老师是看过片花之后很喜欢,通过冯都来找我们,提议我们去参加2013年的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在那个会上杨老师一直陪着我,包括前期我们做一些片花的剪辑,她都给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杨紫烨老师
钱孝贞老师是在我参加的CCDF-3提案会上结识的,当时她很喜欢提案的内容,后来就成为了影片的剪辑兼监制。当我拍了快两年,素材已经差不多的时候,专门去了一趟美国,和她一起工作了几天。在正式初剪之前,我和她一起讨论了整个影片的构架:怎么去讲故事,脉络是什么,人物应该怎样呈现,有什么样的细节可以做的更好。初剪之后是两个半小时左右,已经有一个故事的脉络了,她说我们先“砍树枝”,然后再“绣花”。
第一次她帮我砍树的时候,一下子剪到了80多分钟,我看完以后很心疼,觉得许多喜欢的东西没有了。她告诉我没关系,砍去的树枝可以重新捡回来。但是当我再去修剪的时候,就会思考,为什么她要把这个剪掉,为什么要调整这里的顺序......好的剪辑师会非常准确的去把握影片的叙事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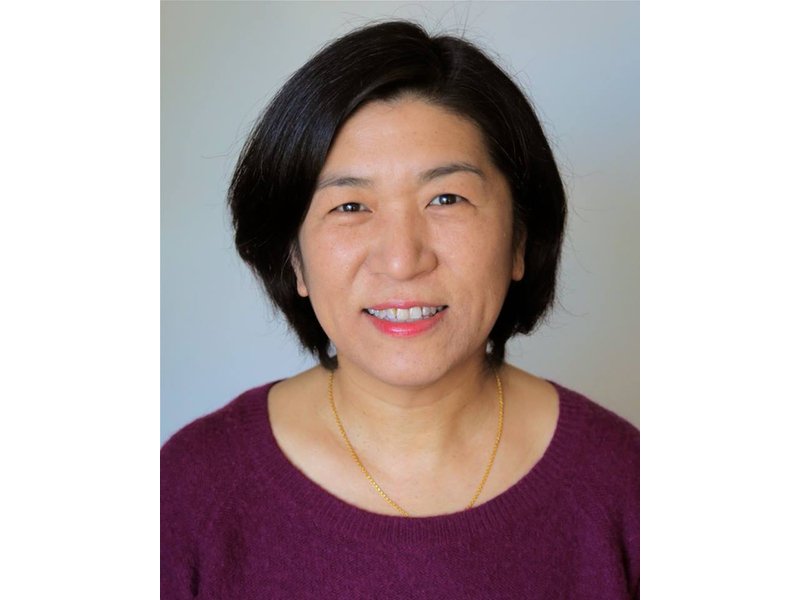
钱孝贞老师
谷雨:您也提到了提案会,你们一共参加了几个提案会?作为一名资深导演,你觉得提案会对影片而言有什么意义?
赵青:有很大帮助。我是第一次在纪录片制作的过程中去参加这样一些提案会,前后参加过CCDF、ASD、HAF、MIDA 、Good Pitch差不多5个提案会。导演在拍摄的过程中其实挺容易迷失的,会质疑自己到底应该从什么点往下走。比如关于纪录片主题,到底应该从两位老人的故事来讲,还是从养老议题来讲?侧重是不同的。通过这样的平台,我们会得到更多更专业的建议,也会慢慢修正自己,重新找到走下去的方向。
冯都:参加提案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项目,有利于之后资金的申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能拿到圣丹斯的资金。另外对于国内的纪录片导演,如果疑惑会不会有国际市场,提案会就是很好的试金石,可以丢出去看看反应如何。我们参加第一次提案会的时候,国际上反应就特别好,所以往这方向走就会更有信心。
谷雨:《我只认识你》在全国各地做了很多的公益放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什么考虑?
冯都:起源是我们参加的最后一场提案会:好提案(Good Pitch)。他们不是把纪录片提案和和电视台买家结合,而是和相关的公益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相连接,也请到了国内的NGO。我们那次就像做了一个试点,得到了一部分专门的启动资金。在拍摄结束后,我们起初是结合上海两家关注失智老人的公益组织,聊上之后顿时感觉像失散了很多年的亲人,他们说:“我们一直想用纪录片的形式来宣传,但找了国外的纪录片来放,效果不好。”后来通过他们,在很多社区、医院和学校进行公益放映。
谷雨:那么就个体观众而言,令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反馈是什么?
冯都:第一场公益放映是在上海的一个药厂,专门研发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药物,当时在座的很多科学家的反应让我特别感动。他们觉得自己很多年以来,都是面对书本来研发,很艰难、很困苦。这个影片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病人家庭的绝望和无助,意识到他们所做的工作特别有意义,也更有动力投入到枯燥的研发工作中去。我当时就觉得,哪怕有一个科学家因为这个片子,研发的动力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很大的进步。
这个影片在社区放映的时候,很多观众会问如何预防这个疾病,怎么寻求帮助?放映之后我们都有相关的医护人员和社区的资源提供给社区居民。社会上已有的一些资源,和有需求的人群,通过影片可以连接起来。
另外,还记得在上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做放映,在场的都是社工系的研究生们,他们会讨论作为社工,未来能为这些人群做什么、有什么创业机会等等。所以能引发不同层面、不同人群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赵青: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群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家属。有一场放映会上,一位老人推轮椅带自己的老伴来,他之前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扛下去了,看完之后却觉得受到了很大的精神鼓舞。这位老人现在和我叔公成了很好的朋友,隔一段时间,他会带着女儿和外孙一起去看叔公,和他聊天。

树锋、味芳参加2015年的上海点映
谷雨:就像一个石子扔进湖面,激起了很多涟漪、很多对话,而不仅仅是一部影片了?
冯都:对,虽然做的不太张扬,但是的确一场一场都在产生很扎实的效力。明年会有更多的线下放映,会推广到更多的城市去。
赵青:每场放映会,不是冯都在就是我在,这一点很重要。真正参与制作的人在现场,去阐述更多,会对观众有更大的启迪和帮助。
做纪录片,是一种生活方式
谷雨:这部片子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导演和制片人是表姐妹,这次合作有没有与以往不同的感觉?
赵青:本身我们就是自家人,拍的也是家里长辈的故事,所以一开始我们之间就有很多沟通,很多想法是一致的。冯都在制片领域也比较资深,参加提案会的时候,也提供给我很多经验和帮助。

(左起)赵青、钱孝贞、冯都于2015年IDFA
谷雨:姐妹俩都选择从事纪录片行业,有没有相互影响、相互激励的因素?
赵青:我比冯都大9岁,在我们这辈里面是大姐,她是最小的。我是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学的是播音主持,但是进了上海电视台之后,很幸运地进了纪录片编辑室这个栏目。九十年代,这个栏目在中国电视纪录片行业中起到非常重要的标杆作用,出了很多很棒的作品。那一代的老师编导,捕捉到了很多社会上鲜活的主题和人物。我是从给这些纪录片配音开始的。从出声音到跃跃欲试想自己拍,从做一些小的纪录片,到自己能独立完成大的选题,周围的老编导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冯都:其实我受我姐影响很大的。小时候她参加很多文艺活动:中学学主持、学艺术体操,但最拿手的是讲故事,经常参加故事大王比赛。有一次我还很小,我爸辅导她怎样讲故事,她就讲了一个“猴吃西瓜”的故事,我就在旁边听,感觉好好听啊。当天晚上,我就给我爸复述出来,他很惊讶。我当时就觉得,讲故事是个很神奇的事情。后来我大学在复旦读新闻,毕业后去美国念书,接触到了纪录片,意识到用影像讲故事,是特别棒的形式。
谷雨:影像表达也有很多种,为什么没有选择剧情片,而是选择用纪录片的方式讲故事?
冯都:那个时候,国内纪录片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纪录片编辑室的《毛毛告状》,颠覆了我对纪录片的看法。原来可以不是“说明文、专题性质,用语言解释,文字配图”的形式,而是讲人物故事。去美国读书之后,人物纪录片也是最打动我的。可能对我来说,真实的人物故事是最有力量的——即便用虚构的形式去讲、即便影像语言更丰富、结构更有设计感,但真实的力量是无法超越的。

纪录片《毛毛告状》
而且做纪录片,对我和我姐来说都不是一个项目而已,而是是一种生活方式。我非常庆幸自己有这个机会,可以介入到别人的生活中,去体会别人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价值观、别人内心的力量,它们会丰富我们自己的内心。
谷雨:理解他人对你来说很重要?
冯都: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在别人身上可以看到更多人的影子,所以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
谷雨:对赵导来说,《我只认识你》是您做的第一部独立纪录长片,与电视纪录片相比,这两种体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赵青:以往在电视台做过的纪录片,大部分都是有点命题作文的感觉,从申报选题开始,到审批、制作、周期,都需要控制,所以不可能有太多的创作时间。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工作。而《我只认识你》完全是我独立出来之后,自己内心想要去做的。一开始的时候,我和冯都都没有太多的压力,就是单纯想要完成它,至于要拍多久,怎么去更好地讲述,都没有太多的概念和限制。恰恰是在这样一种很放松的心态下,可以慢慢去做好它。
做很多逝去的东西,往往是最值得珍爱的
谷雨:赵导提到最初是想通过叔公来挖掘家族故事。我记得您提过叔公这一辈所接受的“孔孟之道”,在你看来是是最“本真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意思?
赵青:我们真的是个大家庭,最早是太外公,1920年代从浙江过来,当时有兄弟两房,几十口人,都住在一个石库门的大房子里。他们从小接受的是很家长制的教育方式,小时候读的都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叔公就是在那样一个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长辈和小辈之间,夫妻之间关系的处理对他影响很大。
影片中叔公带叔婆在西湖划船的时候,很自然地说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一句话就可以代表叔公心目中对“仁爱”的理解,他既是一位仁者,也是一位智者。一辈子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在工作上,生活上、情感上都很坎坷,但还是可以用一种宽厚、仁爱的生活态度对待叔婆、对待他身边所有的事物。这的确是从小的环境氛围在他心中起到的作用。

《我只认识你》剧照
谷雨:这种历经坎坷之后的生活态度,是不是就是您说的“活出尊严”?
赵青:对。两位老人一直保持很干净清爽的外表。叔婆虽然失智,但是可以从很多细节感受到她内心的美好。叔公虽然经历坎坷,但依然热爱生活,喜欢京剧、昆曲、书法......我还要提一个细节,有一次拍摄,叔公居然拿出两把扇子,其中一把是给第一位叔婆的,上面题着“游园惊梦”中的唱词。扇骨都散了、破旧了,他居然还一直珍藏着。当时我很感动,觉得叔公真的是一位非常重感情的人。

赵青、冯都与两位老人合影
谷雨:厚重的家族记忆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一份礼物?
赵青:是的,我决定拍摄这部纪录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多年前,家族中的一位长辈,花了多年心血,完成了我们家族最新的家谱。因为想要做这部纪录片,我很认真地翻阅了一遍家谱。看完之后,更深刻的领悟到做这件事情的价值。很多逝去的东西,往往是最值得珍爱的东西。
突然想起中国著名的女性独立纪录片导演季丹老师说的话:“纪录片就是你活生生地和时间相遇,活生生地和命运相遇。”很多事情你没有刻意想要去记录,只是你遇到了、你记录下来、呈现出来了,真的就意义非凡。
关于赵青与冯都

赵青(图左),1991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之后在上海电视台工作了12年。先后在《上海滩》、《纪录片编辑室》等专栏节目担任主持人、导演等工作,有丰富的电视纪录片制作经验。 2012年,赵青开始拍摄纪录片《我只认识你》,制作期间曾获得2012年第三届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最佳提案奖(CCDF),2013年度亚洲纪录片提案大会最佳提案奖(ASD),影片在2016年的广州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得三项大奖。
冯都(图右),《我只认识你》制片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先后为CNN和BBC工作。她曾获艾美最佳纪录片奖,她参与的作品也曾获得圣丹斯电影节评委奖和美国新闻最高奖皮博迪奖等。 她2008年制片的作品《南京》在国际30多个电影节上获得提名奖项并在全世界十几个国家院线上映,曾一度创下了中国纪录片的票房纪录。她执导并制片的电影《土的味道》曾在旧金山电影节展映并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