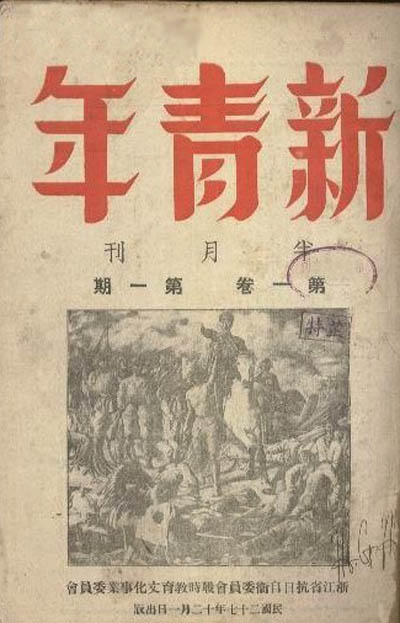
说到新文化运动,便不得不提及《新青年》。从最初的四处谋生,到中期的大放光芒,再到后期成为中共理论刊物,《新青年》走过一条非同寻常之路。在宣传新文化、启迪新思想方面,《新青年》厥功至伟。胡适后来在书信中曾提到,“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然而,《新青年》并非自创刊之日起便名扬天下。从一“寻常刊物”发展成为“时代象征”的期刊界旗舰,《新青年》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成功与其经营手段密切相关。
《甲寅》精神之继承
1914年5月10日,《甲寅》杂志创刊于日本东京,由章士钊任主笔。《甲寅》杂志是《新青年》创刊之前最具影响力的进步刊物之一,并与《新青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研究《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史料。
经济是一切活动的保证,陈独秀在谋划创办《新青年》之前,不得不四处奔波。《甲寅》杂志创刊后,陈独秀也东渡日本协助编辑。《甲寅》后因刊登了《帝政驳论》,遭到查禁。早在“二次革命”之后,陈独秀就来到上海,计划与亚东图书馆创办杂志。因亚东图书馆更看好已具影响力的《甲寅》而不愿投资,创刊计划遂遭搁浅。《甲寅》被查禁之后,陈独秀再次来到上海找到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商议创办杂志。汪将陈介绍给群益书社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陈氏兄弟答应每月支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月出1本,初名《青年杂志》,第二卷才更名《新青年》。由于《甲寅》杂志在当时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创刊初期的《新青年》对其多有借鉴。
在栏目设置上,《新青年》多有因袭《甲寅》的痕迹。如《甲寅》篇首的“政本”,《新青年》的开篇也由政论文构成。《甲寅》设“通讯”栏以便与读者沟通,而《新青年》则安排“通信”栏来和读者交流。《新青年》设“文艺”和“大事记”对应《甲寅》的“文录”和“时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增设“随感录”则基本与《甲寅》一样。
在办刊理念上,《新青年》也是对《甲寅》的继承。陈独秀借“读者之口”表达“自己之意”,通过“通信”栏目,直言不讳地点明二者的渊源。第二卷第一号“通信”栏刊登了“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的来信,来信提到“前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也”。第二卷第二号载王醒农来信,称《甲寅》说理精辟,查禁之后吾辈青年,犹如失去慈母,希望《青年杂志》能够将其薪火相传。第三卷第三号载安徽省立第三中学学生余元睿来信,称赞《新青年》是《甲寅》的继任者。诸如此类的来信有数篇之多,所有这些虽然是读者们的希望,更是陈独秀的初衷。通过阐述《新青年》与《甲寅》的渊源,招揽读者群,宣传新理念。
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被人熟知的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新青年》,在其创刊之初名为《青年杂志》。《青年杂志》意料之外的被动改名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青年杂志》从第二卷开始便以《新青年》的名称面世。该卷第一号篇首登载了陈独秀发表的以“生理心理”而非“年龄”的标准来区分新旧青年的政论,“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新青年之资格也”。陈独秀对“新青年”的独特定位使《新青年》声名鹊起。
第二卷第一号还发布这样一则通告:“本杂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赞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通告》意在说明杂志是应读者的要求而改名,刻意凸显杂志的全新面貌。
当有读者来信询问《新青年》是否《青年杂志》改名而来,若非《青年杂志》改名自己将“弃此不读”时,陈独秀仅简单回复《新青年》即《青年杂志》之变身,二者皆由自己所主撰,并未具体言明改名原因。以至于后来史学家在评价《新青年》改名原因时,认为陈独秀应读者的希望,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这是后人想当然的臆测。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时道明了其中的真正原因。事情的缘起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曾写信给群益书社(前七卷均由群益书社出版发行),指责《青年杂志》(月刊)与他们创刊于1901年的《上海青年》(周报)雷同。出版商陈子寿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官司,商得陈独秀同意,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陈独秀因势利导,利用此次改名机会,调整了编辑方针,使新锐思想更加突出。对改名原因的另类设计与安排,化不利为有利,使杂志因祸得福,彰显了陈独秀的聪明与睿智,《新青年》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炒作:双簧戏的轰动效应
“炒作”是一种非常规的新型传播模式,是现代社会商业活动中一种不可或缺的营销手段。“炒作”是为扩大人或事物的影响力而通过媒体做反复的宣传,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佳的创意和最低的成本,而达到最大化的传播效应。这种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并非当代人所独创,在近代文学史上,《新青年》的编辑同人早已将其付诸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通信”栏,刊发了一篇署名“王敬轩”的读者来信。来信开门见山就鄙视所谓新青年“与夷狄为未足,距禽兽为不远”。因为《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通信”栏中刊载了胡适写给陈独秀的信函,胡适信函批评林琴南所著《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中的“而方姚卒不之踣”不合文法,语句不通。王敬轩的来信正是针对胡适的批评而来。王敬轩力挺林琴南行文无误,并指责胡适不懂古文,瞎乱指摘古文大师林琴南。来函又批评四卷一号所载周作人翻译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才是真正的文法不通。王敬轩指责《新青年》提倡的白话诗随意胡乱用词押韵,不懂中国古文之精深,一味迎合西洋现代文学,数典忘祖。由文学谈及医学,来信还认为西医不如中医。总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泰西均不及中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西学无流弊。另外,编辑部在刊登这篇来信时,全文都是用文言文形式,且不加一个标点符号,给人一种艰涩难读的感觉。
紧随来信的是刘半农对王敬轩的复函,复函以白话文体并标注新式符号的形式予以回击。王敬轩来信仅4000字,而刘半农复函却洋洋洒洒万余言,这在气场上就给人一种压倒优势。复函开篇就说“来信大放厥词”。接着刘半农不无诙谐地说:照先生(指王敬轩)的口气看来,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而后快!然而记者等在逐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一句敬意的话,而且记者等自从提倡新闻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与来信的出言不逊相比,复函似乎显得温文尔雅。复函将来信分成8段,逐条驳斥来函对《新青年》同人的指责。驳斥内容可谓酣畅淋漓,大快人心,似乎是新文化完胜旧思想。但痛骂背后却缺乏更深一层的思考,以至于当真有读者出来论辩时,《新青年》同人一时显得无所适从。其实,所谓署名“王敬轩”的笔者,实际上就是《新青年》六大编辑之一的钱玄同。这在1918年9月5日,任鸿隽至胡适的书信中得到印证。
当来信与复函刊出之后,果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19年初,古文派代表林琴南先后在《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诋毁《新青年》及其同人。接着1919年3月18日,北京《公言报》上发表了《致蔡鹤卿书》,林氏以公开信的形式抨击老北大与《新青年》,蔡元培也通过多种渠道复信辩驳。“林蔡之辩”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新闻媒体将这归纳为“新旧思想之争”。林琴南有意的卫道行为,却不想无意之中给《新青年》做了一次免费宣传。钱玄同、刘半农精心策划的双簧戏,使《新青年》名声大振。
“北上”与“南下”
1917年春《新青年》的“北上”与1920年春的“南下”,在其发展与转型的道途中是两个关键的分水岭。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月出一号,每六号汇成一卷。《新青年》在其创办之初尚面临生存困境,作为一家民营出版机构,经费、稿源和发行是出版商和编辑首要解决的问题,为此陈独秀不得不多方筹划。
前三卷的出版发行,陈独秀得到了乡友的鼎力赞助。如前所述,在创刊之前,陈独秀经多次与好友亚东图书馆老板联系,经后者推荐,群益书社老板才勉强答应每月支付200元的经费。《青年杂志》在创刊号刊登的《投稿简章》提到,来稿无论是独自撰写还是翻译他人著作,一律欢迎。一经选登,即奉稿酬,每千字2元至5元。就第一卷的用稿量来看,大约5.7万字,以平均千字3.5元计算,群益书社提供的200元经费也将用完。《新青年》发行初期,每号印数仅一千册,每册定价2角,每卷六册1元,全年两卷2元。一千册的毛利也才200元,再加上成本,群益书社对于《新青年》可谓是负债经营。乃至于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三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努力交涉,书社方才于年底续刊。初期的《新青年》经营较为困难。
1917年初,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同北迁,这对于扭转《新青年》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陈平原认为,与北京大学文科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
《新青年》前二卷由陈独秀“主撰”,作者主要是陈独秀的同乡学人。其中第一卷几乎是清一色皖籍,第二卷虽然突破了地域界限,但仍局限于陈氏个人的朋友圈。第三卷移师北大之后,虽然陈独秀仍是“主撰”,但随着北大学人的加入,编辑组成员开始发生变化。第三卷有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加盟,第四卷又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王星拱等加入。随着知名学者的加盟,《新青年》稿源不成问题。四卷三号刊登的《本志编辑部启事》宣告,自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同人编辑,不计稿酬。与此同时,杂志的编务也不断调整。陈独秀不再独担编辑,第四卷开始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议,共同商定下一期的组稿问题。大约从第五卷开始,编辑部又开始采取轮流编辑的办法。北大学界群星加盟《新青年》,引起了社会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新青年》遂由一个皖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转变成以北大教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
随着《新青年》的再次扬名,初期的经营困境也不再成为难题。销量也从开始的1000份到最高发行15000多份,《新青年》取得了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借助北大师生的加盟,《新青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在编辑理念上,北大同人都信奉“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不谈政治,但是陈独秀内心深处的革命思想却未曾泯灭,这最终也导致了陈氏与北大学人的分裂与《新青年》的转型。欧阳哲生认为,《新青年》从同人刊物转变为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是五四时期一个具有重要历史象征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意味着杂志本身办刊宗旨及内容的重大变化,而且反映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刊物的主导者,预示着“五四”后中国新思想的主流有可能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六号,先后发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第六卷第五号设《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了李大钊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学说。该卷还刊登了其他作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稿。《新青年》成为了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讨论的论坛。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新青年》趋向革命的思想日渐显著,这与北京同人的编辑所信奉的不谈政治的编辑理念相冲突。陈独秀与北京同人关于编辑方针转向讨论的信函往来颇为频繁。
1920年春,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年》也随其迁回上海。1920年5月,《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因篇幅过多,群益书社要求加价出售,陈独秀反对,从而直接导致了《新青年》与群益合作蜜月期的终结)。7月,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为发起人。与群益和北大同人的分裂,使得这一时期的《新青年》再次面临困境。而共产国际东方局的适时帮助和新一批共产主义者的注入,《新青年》再次重塑形象。9月,《新青年》又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1920年秋,《新青年》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准备付印时,因刊载了《阶级斗争》、《到自由之路》等比较敏感的文章,而遭法国巡捕房查禁。1920年底,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赴粤,《新青年》也南下广州。1922年7月出满9卷后休刊。1923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已然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1926年7月,《新青年》终刊。
《新青年》的成功离不开独具匠心的编辑同人的智慧。《新青年》创刊期间,借助乡谊之力得以艰难运营。陈独秀任职北大之后,凭靠北大这一文学重镇,使《新青年》得以大放异彩。出其不意的营销手段成就了《新青年》非比寻常。后期的转型,虽然使《新青年》脱去了鼎盛期的光环,但在掀起新思想方面却走得更远。无论从文学史、思想史还是政治史的角度进行评价,《新青年》都将给后世人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原题:《《新青年》的经营之道》

